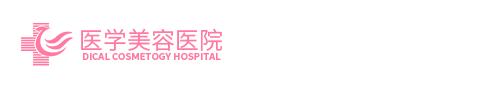安博体育游戏

”)最初的举办者为亚兴置业。2009年7月28日,亚兴置业与安博教育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将目标学校的教学举办权、经营收益权(不包括转让交割前的历年结余额)、经营处置权、无形资产等以及截止协议签订之日目标学校正在使用的教学设备和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教学楼的房产作为转让标的权益(以下称标的权益)转让给安博教育,转让对价为人民币16779万元,其中人民币8391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其余人民币8388万元以安博教育控股等值待上市的股票的形式支付到亚兴置业指定的海外公司。双方为履行《合作框架协议》,另行签订了《权益转让协议》、《房屋及场地使用合同》、《关于收益分配及资产保障的补充协议》;双方海外的关联公司签订了《股权购买协议》(以下统称附属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安博教育以现金和股票的形式支付
2012年1月4日,亚兴置业向湖南长沙教育部门提交了《关于请求终止与安博教育集团合作协议并收回同升湖学校及幼儿园举办权的请示报告》,要求终止《合作框架协议》并收回目标学校的举办权及其他所有权益。2012年1月29日亚兴置业向湖南长沙教育部门提交了《关于安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南长沙同升湖学校的各种违法违规事实的专题报告》,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对安博教育集团以外资身份进入义务教育领域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2012年6月26日,亚兴置业向湖南长沙教育部门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撤销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做出的关于批复目标学校变更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期限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其申请,亚兴置业就该行政复议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以同样理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无奈之下,亚兴置业于2013年向湖南省高院提起本案诉讼。
从诉讼策略来看,亚兴置业选择将《合作框架协议》作为诉讼对象,而没有将VIE协议作为攻击目标,原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亚兴置业并非VIE协议的当事人,该等协议也并未直接涉及亚兴置业希望返还的目标学校各项权益,如果仅仅选择VIE协议作为诉讼对象意义不大,法院也可能直接驳回起诉。其次,《合作框架协议》并没有就争议的管辖进行约定,从而给亚兴置业选择在湖南当地提起诉讼提供了机会,而VIE协议约定的管辖可能并非亚兴置业所愿意尝试的。从诉讼主张上来看,亚兴置业的核心主张是《框架合作协议》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法定无效情形,应属无效。从这一请求权基础来说,亚兴置业需要着力证明的事实要件为:
湖南省高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安博教育与安博在线公司之间的协议安排仅系将目标学校的经营收益转移至安博在线公司,也就是说安博在线公司所实际控制的是目标学校的经营收益,而并不涉及控制目标学校的教学安排,目标学校的教学安排仍然必须按照我国有关教育政策贯彻实施,作为内资企业的安博教育负有严格遵照我国公司法和有关教育产业方面的法律、政策对目标学校的教学安排予以管理的法定义务。根据安博教育对目标学校接管后五年多时间中目标学校的运营情况看,并没有发生因为安博在线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而对目标学校的教学安排施加不当影响的情况,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仅仅因为安博教育将目标学校利润的转移至安博在线公司即会导致目标学校的教学安排被外资控制,从而危害到我国的教育产业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博教育与安博在线公司之间的利润转移协议并不违反我国对禁止外资进入我国义务教育领域的立法本意”。由此可见,湖南省高院首先认可我国法律是明确禁止外资进入义务教育领域的,但对此明文规定并非直接适用,而是主动探究VIE协议的实质目的及禁止性规定背后的立法意图,从而为VIE协议的正当性提供了一定支持,这可以说是VIE结构的福音。
最高院在二审判决中对一审法院和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的上述观点并未明确表示意见,只是表明“对外资通过并购股权参与举办或者实际控制举办者实施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的行为,可能存在危害教育安全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对可能存在的外资变相进入义务教育领域,并通过控制学校举办者介入学校管理的行为,应当予以规范,并通过行政执法对违法行为予以惩戒。就此,本院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该部在行政审批及行政监管过程中,对此予以依法规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教育安全。”教育部作为教育领域的最高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最高院的司法建议后是否会对教育领域,特别是义务教育领域的VIE结构采取相应的执法和监管措施,我们暂时不得而知。在司法实践中,最高院向政府部门发司法建议并不常见,通常是在审判活动中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建议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由于我国法律对政府部门收到法院的司法建议后具有何种义务或者应履行何种答复程序并无明确规定,这也导致实践中政府部门收到司法建议后可能不会做出任何进一步的举动。
从最高院对本案的二审判决书来看,尚无法推断其对于义务教育领域存在的VIE结构合法性的意见,更无法据此预测其对其他领域涉VIE结构的案件将如何裁判。本案对于涉VIE结构交易的启示可能在于:首先,目前法律和司法裁判对于VIE结构的合法性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在考虑VIE结构和有关协议的安排和设计时,需要更多地探究我国法律对某些领域进行禁止或限制的立法本意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态度,尽量避免触及相关法律所保护的“核心利益”,从而为其合法性提供更多的辩护空间。其次,从个案来看,VIE结构的法律风险主要来自VIE协议或者有关交易文件各方的争议,尤其是当这种争议被诉诸法院而被公之于众时更是如此。因此,在设计VIE的结构以及起草相关交易文件和VIE协议时,需要妥善设计VIE实体的控制权、并对参与签署文件的当事人、交易文件涉及到VIE结构的最低限度、有关争议解决条款等方面进行精心的安排,尽量避免VIE结构被诉诸争议解决,尤其是法院诉讼。